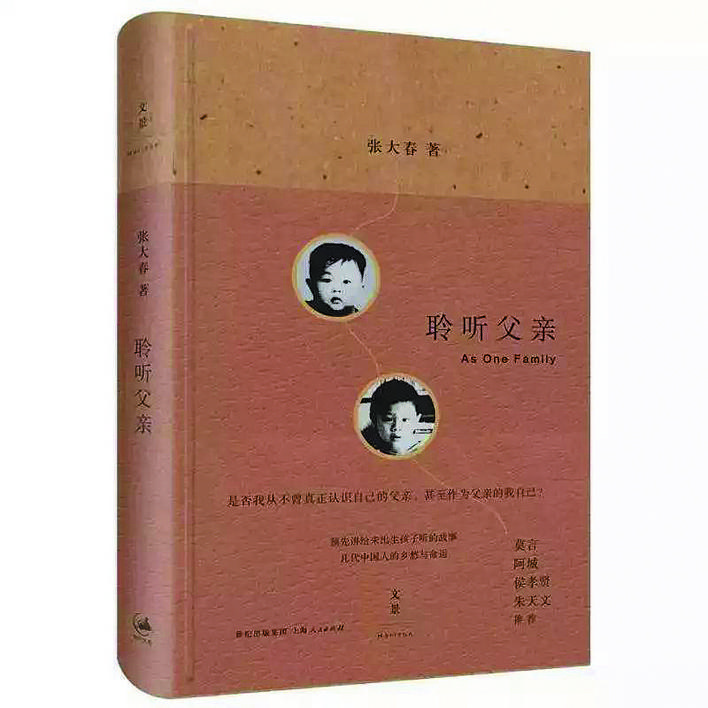
是2008年的某一天吧?在书店里闲逛,撞到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聆听父亲》。前书腰上“莫言、李锐、阿城、侯孝贤、朱天文倾力推荐”的字样,没有说服我掏腰包:这年头,还有不拉名人推荐来出的书嘛?!后书腰上朱天文的几行字,倒是一下子把我攫住:“第一次,他如此之老实。甘心放弃他风系星座的聪明轻盈,有闻必录老实透了地向他未出世的儿子诉说自己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第一次他收起玩心不折不扣比谁都更像一位负责的父亲。第一次他不再操演他一向的主题——真实/虚构。第一次,他暴露了弱点。”
2007年9月,几近皮包骨的父亲,终没抵过病魔的摧折,走了。人到中年,参加过几起葬礼,听到过更多的死亡。当时,是感伤;几日过后,那感伤就给忙碌的工作、琐碎的生活稀释,转淡,消逝。父亲的远去,却让我一下子失了神,不知所措。他在的时候,是一堵墙,为我遮风雨、挡冷凉、抵死神;他走了,我给一下子推到风雨、冷凉、死神面前。
那些日子里,极力不去想他的不在,想以这般的不想,来抗争巨大、无常且冷冽如月光一般的命运对他生命的掠夺,来幻化他在我世界里的永在。
我对父亲去世,这般反应。别人呢?这本书的作者张大春呢?莫名的好奇心、强烈的无助感,推着我掏了钱,买书,走人。
夜里,窝在床上,翻《聆听父亲》。白纸黑字的缝隙里,不时会枯墨洇宣纸般地,隐显出父亲的音容,以及他之于我的种种。唏嘘不已的当儿,一点一点学着臣服,学着接纳父亲的渐行渐远。
这书写得,够有勇气。这勇气,不是面对强权或蛮力时的不退缩,而是看见生命实相时的不扭过头去的体察。作者这样写父亲摔倒后他给父亲洗澡的情形:“我继续拿莲蓬头冲洗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几近全秃的顶门、多皱褶且布满寿斑的脖颈和脸颊、长了颗腺瘤的肩膀、松皮垂软的胸部和腹部、残留着枣红色神经性疱疹斑痕的背脊。”这种丝毫不为垂垂老矣的父亲讳,手术刀般,挑开人生真相,是不悦目,却让人难免眼窝发热,鼻子泛酸。书中,作者写到他在大学里作为合唱队队员合唱完发现自己痛快地流下泪来时,这样感慨:“逼近艺术,就像逼近实情真相一般,令人脆弱。”写《聆听父亲》时,张大春就是逼近实情真相,边写边哭。他这样说这本书的写作:“从来没有哪本书写完有被掏空的感觉,这是第一次。”他之所以有被掏空的感觉,就是因为他暴露了自己一直在掩藏、一直不敢触碰的那一块。坊间,我们不缺神游八极、才气横溢的才子,也不缺旁征博引、演绎推理的学者,不过,有勇气逼近自己内心最脆弱的那块的,不多。难怪朱天文把她那篇点评本书的书评,命名为《弱点的张大春》!
这书写得,更够老实。张大春写他曾祖母的家规,说:“绝大部分——非常奇特地——与做人处事、修身齐家的大道理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多是像“煮老猪、老羊,要往锅里扔一把旧竹篾子须;煮老鹅,须放灶边陈瓦同煮;煮老鸡,赤锡两块,其烂如泥”这样素朴的日常生活小窍门。就是他父亲跟他讲“一件事情跟另一件事情要厘清”这样的大道理,也直白得让人咋舌:“大便入坑、小便入池,别搅和。”至于他十六七岁被拒的恋爱,是这样给传真过来的:回他情书的那个女孩对他的情书“用红笔胡乱圈点一阵,并且极尽嘲诮之能事地夹注、眉批”,对他邀她看《西城故事》的诚意,她寄给他二十块钱,其中一张钞票上写着“请自便”三字。作者十六七岁的那个年代,“请自便”就是“请自行料理大小便”的意思。最后,作者这样回击嘲讽他的爱慕对象:“一个他妈的不会被甜言蜜语款款深情打动的女学生。”是呀,失恋了,几人会有“恋人不成做朋友”的大度呢?!
说这书写得老实,是就内容而言。说到技巧,张大春是一点也不老实了;他根本没有像朱天文说的,“甘心放弃他风系星座的聪明轻盈”。整部小说,头绪繁多,每条线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时间上,不是直线发展的顺叙,也不是尚算老实的倒叙,而是将来、过去、现在这几条线,左、前、上、后、下、右,交错。这般绕迷宫一样叙述事件发生的间隙,时不时地,还夹杂上对《诗经》、《古诗十九首》、《家史漫谈》、希腊神话等等的引用,更夹杂上对写作、认知、京剧、音乐、历史等等的思考。这种一本书里讲故事的人和博学的杂家穿插出场,让人油然想起读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时历经的惝恍迷离。
本书上架建议,是小说。而我,更愿意把它当散文读。据报道,有记者问张大春:“你全书交织个人记忆、家族历史和大历史,该视之为自传或是虚构小说?”居然,小说家张大春说:“当成长篇散文看吧。”
把这书当散文读,较之当小说读,确实能更好地领悟作者的情感与思考。读这书时,时不时地,会被张大春激发。读到张大春引用《古诗十九首》谈生死时,不禁想起曾读过的小埃德加· M ·莱利(Edgar M. Reilly, Jr.)那篇讲自然界生态及其代谢的文章 《生生,死死,生生》(Life and Death and Life)。那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我们在树林和田野中穿行时,便能碰上各种动植物的遗骸。有些我们看不到,因为残留下来的已经被枯枝落叶所覆盖。还有一些躲过了我们的视线,因为它们在枯干的过程中变了色,而死亡所产生的那种腐烂气味又被种种新的不同的生命气息所掩盖……人类小心翼翼埋葬的一代代先辈最终也会被腐烂的力量,亦即生命的力量,所消解……死亡即生命;只不过由于生命的旺盛,死亡难以为人所察觉罢了。”
进而,想到父亲去世五七时的情景。父亲入土时,坟墓周边的麦苗刚露绿尖。等他去世五七时,那麦苗,已长到脚踝。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那些逝去的亲人,已如此般,化成了麦,化成了草,化成了树,化成了花……
清明又来,小麦、绿草、大树、鲜花,绿肥,红亦不瘦。却原来,那是我们思念的亲人,以另一种面容、另一种身姿,与在世的我们,再相见。
李献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语教学中心
2024-03-15
文章来源:https://newspaper.hf365.com/hfwb/pc/content/202403/15/content_452637.html
